阅读:0
听报道
最近,一个冷涩的经济学词语成为国内财经媒体追捧的“热词”,这个词就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这个词汇脱胎于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的渊源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初的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依(Jean-Baptiste Say)。萨伊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写下了著名的“萨伊定律”,它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
现代“供给学派”的诞生则要等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是凯恩斯主义,但在凯恩斯主义的理念下,西方各国一味扩大需求,导致社会经济停滞、物价却反而持续上涨的背离局面,也就是“滞涨”。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提出了不同的经济治理思路,其中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为代表的一群学者,从凯恩斯主义的反方向提出应当依靠降低税率、提高生产能力等措施,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基于此,在现代“供给学派”中,降低税收即成为核心观点,这一理念在80年代成为里根-撒切尔政府应对经济萧条的主要手段,并帮助英美两国走出阴霾,迎来一段较长时期的增长。
不过,仅仅依靠税收这样的单一手段而实施的“供给侧改革”,如同“萨伊定律”一样带有先天缺陷。在实施初期,降税确实帮助西方国家改善了状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财政赤字也随之加大,社会贫富差距更是明显扩大。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此后的英美两国再度抛弃“供给学派”的理论,重新投入到凯恩斯主义的环抱之中。
如今,30年过去。最近的30年是人类文明史上变迁最大的30年。正是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信息技术革命,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许多人将这场变革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有西方媒体将这场变革命名为“新经济”;托马斯·弗里德曼则把今天的世界称为“被抹平的世界”;还有学者将其称为“第二次机器革命”(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无论用什么充满噱头的名词,来描绘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得承认,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上一次工业革命促发的产业模式和经济形态都正在或者起码也是在不久的将来,将被视作“旧经济”,而千万种新的经济模式正在我们的身边迸发出来,却仍未给我们带来明显的福利。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在整体上暂时陷入了瓶颈,这种困境连同2008年突发的金融危机,令全球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就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所感叹的,那个“低垂的果实”已被采摘殆尽的“大停滞”时代。面对这种背景,中国政府却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的时候,再度拾起“供给侧改革”这个被西方经济学家压在箱底的理论,显然不是在简单地“拾人牙慧”,其中一定有着不同于此前任何“供给学派”学者的新内涵和新考量。
想要理解这种新的内涵,我们或许可以从3位美国学者撰写的《资源革命》一书中窥见一丝端倪。
《资源革命》一书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来入手,来探讨变革发生的根本原因。“罗马俱乐部”在著名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曾悲观地预测,如果不采取紧急的环保和节约措施,科技发展的速度将无法赶上人类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的速度。这一近乎 “末世论”的预测,也正是《资源革命》想探讨的话题。

同样《资源革命》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将给全球带来25亿的中产阶级,这意味着在能源、交通、建筑、水、农业、金属以及各个方面,将对产生巨大的资源需求。如果按照传统的产业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当然无法承受如此巨大规模的需求增量,这也令“罗马俱乐部”的“末世论”看上去有一定道理。
但出人意料的是,与“罗马俱乐部”的那些精英研究员们不同,《资源革命》的作者却采取了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整合,会改变人类生产和使用资源的方式,这种改变带来的“资源革命”,将会为人类解决这一“囚徒困境”。
为此,《资源革命》进一步提出了五大“革命”原则:资源替代、减少浪费、提高“可循环性”、最优化及虚拟化。资源替代即是寻找可替代能源,页岩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开采和利用增强了化石能源的可替代性,当然风能、光伏等清洁能源就是更加典型的例子。
智能电网带来的变革,则是用来说明“减少浪费”的最好案例。传统的电力传输技术,电力能源的损耗比例十分大,在特定时间里,只有20%-40%的电力传输能力得到使用,但是在智能电网模式下,电力使用效率将获得极大的提升,并且电力的超远距离运输也将能够得以实现。这恰恰正是中国国家电网目前正在构建的特高压电网想要努力的方向。
提高“可循环性”自然也不难理解。对于现代人来说,资源的循环利用技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随着废旧金属、电子产品和水处理技术的更新迭代,资源循环利用的效率和成本也将大大的降低,这自然也将有助于缓解资源紧张的状况。同样,在这个过程中也蕴藏着巨大的产业机遇,麦肯锡的研究发现,光是通过翻新和重复使用电子产品,每年就可以创造9000亿美元的产业机会。
最后两点“最优化”和“虚拟化”或许比较让人费解。事实上,这两个特征也早已存在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能帮助我们理解“最优化”的例子就是系统整合。例如优衣库、ZARA等快消巨头重新设计了服装产品的生产、销售流程,它们在革新行业模式的同时,也使得自己成为服装业中的“新贵”;而中国远大集团在建造摩天大楼的过程中,实施的模块化改革,也同样给建筑行业带来了革命性变革。
更重要的是,在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技术加速融合的今天,流程再造不仅意味着生产和销售过程的再造和重组,也意味着如何将新的技术和模式运用到传统工业企业中。这样的举措和努力,在德国被称为“工业4.0”,中国则称其“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在美国则叫做“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名字不同,本质上却大体上讲的是类似的内容:如何借助互联网工具和智能设备,去改造甚至于颠覆旧的生产流程,并设计出新的流程,以更高效地调动各类生产要素,生产出精准地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正如《资源革命》所说,“只要方式正确,系统整合就意味着1加1等于11”。
最后,在这样的智能制造改造过程中,生产和生活的虚拟化也就成为现实。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为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重新构建了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现实世界互联互通。所以,在无人机可以替代士兵奔赴战场的时候,那些虚拟的工具和机器人也能为人类的生活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巨头正是这个虚拟世界里诞生的第一批商业巨头。
诚然,《资源革命》更多的是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阐述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机遇。但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到,“资源革命”恰恰就谙合中国当下实施的“供给侧改革”的改革逻辑。
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十一次会议上指出,“供给侧改革”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过剩产能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这一举措的背后正是“中国制造2025”规划以及“互联网+”战略的实施。11月23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中,则更具体地指明了产业优化重组的方向和内容:培育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加快可穿戴设备、电子商务等产品和服务的发展,都成为了题中之义。
这就意味着,中国今天推动的“供给侧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产业优化,来摆脱“大停滞”的危险,而带领我们走入新的繁荣。这一目的也正与《资源革命》中提到的那五大模式努力的方向相吻合。
所以,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企业发展,想要摆脱“大停滞”的困境,创造新的繁荣,就必须投入到技术和模式的创新之中,来契合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推动产业的优化和升级。就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指出,“当繁荣成为美好生活的流行概念时,美好经济必须帮助人们想象和创造新事物,从而实现创新。”
这样来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本质上就是鼓励全社会打造出新的经济模式,以此贴合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对此,我们或许不需要像《资源革命》所“奢望”的那样,去拥有100年后主宰世界的12大产业;更重要的则是,今天的“资源革命”或“供给侧改革”,能够为我们倒逼出一个更为治理更为科学的政府、一个更为透明和健康的市场环境,以及一个充满活力和乐观的创新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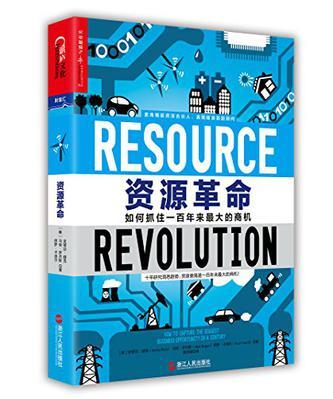
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帮忙在“朋友圈”转发,并推荐“严杰夫的约柜”。:)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