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上月21日在第二轮投票中通过了包含实行总统制在内的宪法修正案,倘若在几个月后的全民公投中获得通过即可生效,土耳其政体将出现由议会制改为总统制的实质变化。许多观察家认为,一旦这种变化发生,土耳其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或将成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之后现代土耳其“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有人甚至评说,“埃尔多安王朝”已呼之欲出。
作为一个号称“温和派”伊斯兰政党领袖,埃尔多安在执政后就一直备受争议。尤其去年7月爆发的土耳其武装部队政变,这类质疑达到顶峰。尽管这次政变很快被平息下去,但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今天土耳其社会内部的分裂已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
与巨大的社会裂痕相对应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土耳其国民经济始终萎靡不振,近几年更出现了恶化趋势。2016年经历了多次恐怖主义袭击,土耳其经济更雪上加霜。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2016 年土耳其产出增长预计将下降2.9%,而其国内的通胀率却高达8%。有机构测算,若从2016年1月算起,土耳其里拉对美元已贬值逾15%,即使在外汇市场上货币表现最差的“脆弱五国”(Fragile Five: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和印度)里,土耳其里拉的表现都是最差的。
土耳其在上世纪后半叶曾被誉为伊斯兰世界的“模范生”,为何在进入21世纪以后,却逐渐沦为全球经济体中的“差生”?这恐怕需要从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土耳其学者悉纳·阿克辛的著作《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就提供了不少解释。阿克辛这部著作似乎并非对土耳其转型道路抱以批判性目光。这可以理解,这部著作出版时,埃尔多安刚踏上土耳其政治舞台,土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尚未遇到如今的困境。所以,作者并未过多表露出对土耳其未来的担忧,反而许多时候还常常会流露出“土耳其式”的民族自豪。但读者今天展读,自会生出另一番感触。

阿卜杜勒·哈密
如果用更为宽泛的历史眼光来考察,土耳其的现代化转型是从奥斯曼帝国末期开始的。按阿克辛的标准,土耳其或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起码可追溯到1789年塞利姆三世苏丹的登基。在塞利姆苏丹统治时期,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奥斯曼帝国开始实施军事改革。1793年,塞利姆三世设立了一支以法国大革命目标为名称的新式军队――“新秩序”。但是,塞利姆三世的改革仅局限在军事领域,却令已被边缘化的帝国禁卫军地位进一步遭到威胁。因此,禁卫军在1807年爆发叛乱,塞利姆三世因错过了镇压时机而遭到废黜并被处死。尽管塞利姆在位时间不长,但其主导的军事改革却重造了帝国军队。此后,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不再需要像之前那样通过中间人“阿扬”(地方势力)来招募士兵,新式军队成为帝国核心的军事力量。
奥斯曼帝国更广泛的改革发生在阿卜杜勒·哈密统治时期(1876年-1909年)。尽管阿卜杜勒的统治在历史上以“警察国家”著称,但在这一时期,奥斯曼成立了议会,并在形式上实施了君主立宪制,阿克辛将其评价为“土耳其走向民主的里程碑”。也是在此期间,帝国拥有了银行、社会保障基金、职业和工业学校体系等现代机构,这些组织机构有些直到现在仍在发挥作用。可以说,奥斯曼帝国迎来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1874年,在阿卜杜勒就任新苏丹的前两年,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建成了国内第一条地铁,这是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古老的城市地铁,直到今天这条线路依旧运行在加拉太桥到独立大街之间。

Tünel:伊斯坦布尔最古老的地铁
除去这些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成就,阿卜杜勒统治时期还发生了一桩重大历史事件。这决定了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土耳其的转型道路。这就是1889年统一进步协会的诞生。起初,这个协会是由五名伊斯坦布尔军医学院学生组成的秘密团体,主要活动是阅读自由派作家的作品。但统一进步协会却对土耳其现代化提供了两大贡献:第一,孕育了土耳其的伟大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第二,提供了土耳其主义这一全新观念。另外,阿克辛还认为,正是由于统一进步协会,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才坚定走上世俗主义。
总的来看,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改革,已为土耳其转型指明了方向:努力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但作为统治者的苏丹,既不愿在实质上放弃君主专制,又想继续维持帝国疆域的统一,遂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帝国晚期所实施的改革措施大多浮于表面,无法在根本上改变奥斯曼帝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所以,晚期的奥斯曼帝国已沦为西方附庸,只能依靠在列强中实施平衡外交策略,来维系生存。
即使是这样的艰难局面,也随着一战而崩溃了。这场大战不仅摧毁了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制,也令整个帝国分崩离析。独立运动领袖凯末尔,在革命中乃至后来的执政过程中,采取土耳其主义作为国家决策的根本思想,可说是基于土耳其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而作出的现实考量。这一指导思想,不仅在帝国分裂局面下尽可能地统一起土耳其人民来反抗列强的入侵,也推动了土耳其在独立后立刻走上世俗化道路。而这也使土耳其主义在凯末尔成为土耳其“国父”之后,被称为“阿塔图克主义”或“凯末尔主义”。
在很多学者看来,凯末尔主义抛弃了奥斯曼主义,我却认为,尽管从根源上来看,凯末尔主义诞生于统一进步协会的理念,但在本质上还是对奥斯曼主义的一种继承。它们在目标上其实都是要建立一个“欧洲国家”,亦即西化。两者间仅有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凯末尔主义迈出的脚步更彻底、更激进,而奥斯曼主义却还带有“中世纪式”的包容。

穆斯塔法·凯末尔
凯末尔主义在坚持“西化”进程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从二十年代开始推行的“帽子改革”。1925年11月,土耳其制定了《帽子法》,以废除作为奥斯曼标志的“费兹帽”。从那时起,“费兹帽”便从土耳其民众的头上消失了。尽管这一举动在外国人看来有些“小题大做”,但土耳其人却明白其中意味深长的含义。阿克辛评论说:“帽子改革”成功传递出了“我们是欧洲人,不会成为殖民地”的信息,而对土耳其人来说,这更意味着“土耳其将成为一个欧洲国家”。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凯末尔的改革和政策带有丰富的目标和内涵,我却认为,只需用两个字就可清晰概括,那就是“西化”。可以说,这一目标也成为凯末尔之后,所有执政者的政策导向,甚至唯一导向。以至于“西化”成了土耳其此后历任政府新的“信仰”,再也容不下其他理念和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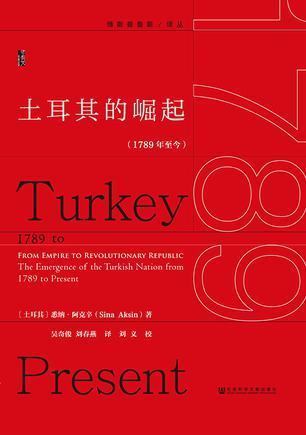
凯末尔继任者伊诺努在政治上推崇多党制,却对国民经济实施管制干预;20世纪50年代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在很多政策上都表现出反对凯末尔主义倾向,但在“西化”问题上却与前任表现出惊人一致,在他们的任期内,土耳其迅速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0世纪80年代的厄扎尔政府,更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完全照搬西方经济政策,甚至成为西方政策的傀儡;而此后,成为“欧盟成员国”又成了每届土耳其政府的核心目标。
或许,对土耳其来说,“西化”是条相对现实的现代化路径,但当这条路径逐渐异化为政策唯一目标甚至在决策中占据垄断地位时,就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所以,无论民主党政府,还是阿扎尔政府,乃至于今天的埃尔多安政府,都始终难以为土耳其制定出理智且有效的经济政策,以应对土耳其建国后经历的每次经济危机,更没能让土耳其国民享受到“国家崛起”带来的经济福利。正如约翰·伯格上世纪80年代在伊斯坦布尔旅游时所观察到的:来自安纳塔利亚的劳工和农民,与“有钱中产阶级”一起汇合到这座土耳其最大的城市里,但他们之间却泾渭分明。约翰·伯格对土耳其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直观反映了土耳其在过去200多年转型过程中,在改善阶层分化的问题上收获甚微。
所以,今天土耳其社会不断爆发的分裂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民众对政府长期以来“误解”并实施“西化”政策的回应。正是由于多年来执政者不断将凯末尔主义极端化和异化,自奥斯曼帝国晚期开启的“西化”道路至今依然曲折迷离。
----------------------------------------------------------------------
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请帮忙在“朋友圈”转发,并推荐“严杰夫的约柜”。:)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